在文学写作尚未成为稳定经济来源的时候,“我”以送报员的身份赚取日常开销。太阳微亮时,“我”驾驶电动车穿行在西安城南城北大街小巷送报;工作结束后,就将车靠在就近图书馆、书店的位子,赶紧摊开书,继续意犹未尽地沉浸在文学阅读中;回到出租屋后,又一头扎进了纸笔间,构思着自己笔下的人物和故事。主人公“我”是辛峰的生命镜像,他自身的记忆与过往,也借由《西漂十年》的叙事,重新演绎了一番。
“十年来,我的单车滚过城中村的角角落落,也把青春如同水银泻地般洒遍了所到之处。在北山门,我努力挣脱稚嫩的学生面孔;在瓦胡同,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最卑微的报童;在和平门与龙首村,我在文学青年与底层民工之间不停地转换角色;在张家堡,我试图彻底地沦陷,以堕入地狱般的放逐,寻求向天堂上升的阶梯。”
《西漂十年》的尾声,辛峰以“告别城中村”为章节名,为自己的青春和经历的西安十余年的变迁画下故事的句点。
03十里庙岭:故乡的回望与审视
“我写散文,常常是兴之所至,情之所发,当内心有了一种无法遏制的创作冲动和表达欲望的时候,散文也就自然而然从笔端流出。
如今已经搬离城中村的辛峰,近年来撰写了数百篇自我表达与经历审视的文章,在《文艺报》《延河》等知名报刊上陆续刊登。这些作品中占比最多的内容,都与辛峰的家乡——庙岭村有关,“庙岭在我无意识写作里,竟然成为了一种冥冥之中的意识。”
察觉到这种自身与家乡命运牵连的巧合后,2023年底,辛峰决定以“庙岭村”为名,将散文内容中关于故乡与往事的部分归纳出版,取书名为《十里庙岭》。“一个伟大的作家,可能终其一生都在写他的童年。”他说。

《十里庙岭》辛峰著
庙岭村,这片在中国地图上只有微小标记的黄土地,几乎浓缩了辛峰18岁之前的全部人生。《十里庙岭》从1981年辛峰在老窑洞呱呱坠地开始,讲述了春风里母亲的白发,盛夏乡野间生命力旺盛的野生蜀葵,漆黑隧道内秋虫的歌声,魔术师般的关中大雪……在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织共存的复杂历史语境中,辛峰试图用自己内心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来做一次深情的回溯,并以此为基石,走向人类必然要面对的现代文明的书写之中。每一篇串联在书中的故事,都透露着辛峰对“土地与故乡”的深沉理解与厚重的历史反思,以及年华逝去、回首过往的些许感怀。
庙岭村之于辛峰而言,“承载自己少年时期的人间悲欢,也是自己不惑之年对过往的深情回望与打量。”现在回忆起来,“虽然那个时候的很多感触连自己都已经模糊不清,可当我考上大学,一步步走出这片黄土地时,日渐远离之中,它却在我的眼前一点点变得清晰和真切起来。”

辛峰在家乡庙岭村留影
在西安求学和生活的20多年间,辛峰曾面临诸多如《西漂十年》里主人公“我”所经历的“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所导致的心灵的挣扎和生活的困顿”。
但是,他并没有因时代的不确定发展而迷失自我,“我知晓身后永远有一片可供我栖息和休整的根据地,那就是父母亲人所在的那个叫“庙岭”的小村庄,甚至,我之所以能有在《文字的风度》中的沉潜和奋发、宁静中的思考和内心里的清凉,均是得自那一方厚土的恩赐。”
04文学坚守:寻找明亮的微光
如今,年过不惑的辛峰笑称自己“不可避免地随着年龄增长被岁月赋予沧桑”,这种“沧桑”也让他的写作体系在多年的人生经历与文学摸索中“走向成熟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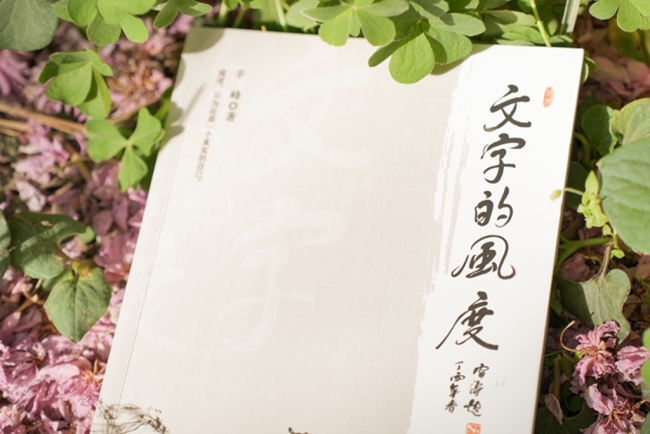
《文字的风度》辛峰著